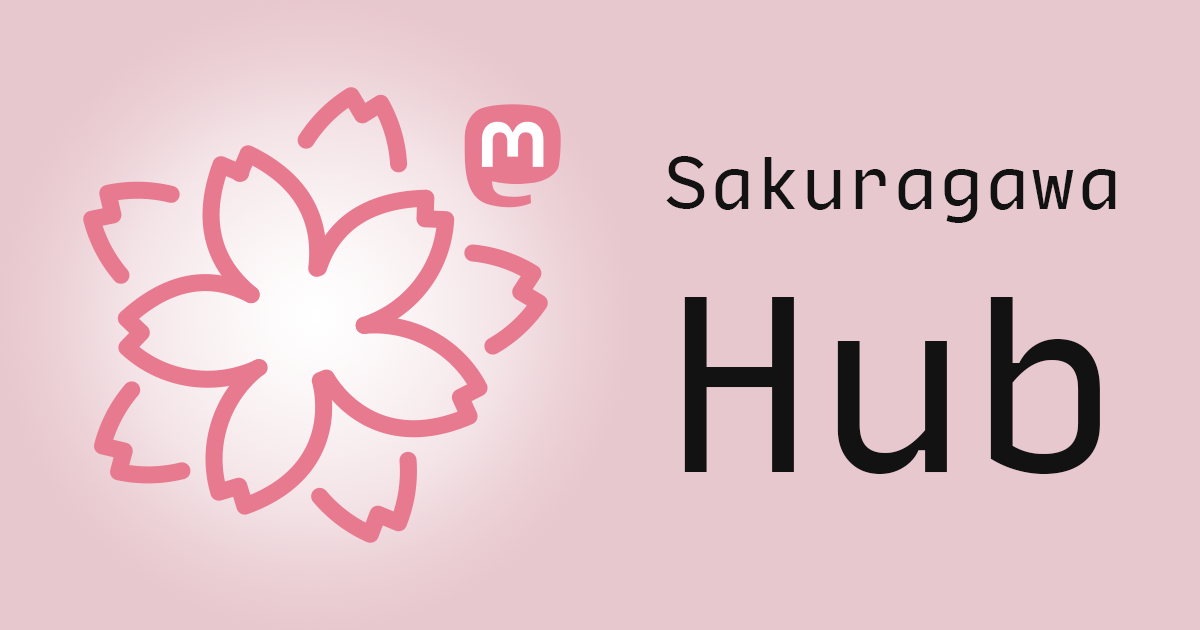鹹:「賣點沒用的東西搞點錢。」
甜:「可以賣我。」
鹹:「那有誰要呢?」
#鹹甜日常 殺人還要誅心啊
少数派年度离谱文章出现了:
这是为所有女生设计的一款提升自我的软件
https://sspai.com/post/85399
省流:作者提出的女性提升自我项目为:清晰下颌线、全面的面部矫正程序、精致少女脸、矫正大小脸、双下巴消失术……等24个(初期规划版)美容动作
看着 partner 換了新 #iPhone,我流下了想要遙遙領先的淚水
@JJoe 這個麵光看起來口感就會很好
2024 年了!
There are a number of Mastodon apps for old computers of the 1980s and 1990s:
![]() Apple II
Apple II
https://www.colino.net/wordpress/en/mastodon-for-apple-ii/
![]() Apple Macintosh (pre-OS X)
Apple Macintosh (pre-OS X)
https://github.com/smallsco/macstodon
![]() Commodore 64
Commodore 64
https://github.com/Havoc6502/MOStodon
![]() Commodore Amiga
Commodore Amiga
https://github.com/BlitterStudio/amidon
![]() MS-DOS
MS-DOS
https://github.com/SuperIlu/DOStodon
![]() MVS
MVS
https://github.com/mainframed/BREXXTODON
:Palm_OS: PalmOS
https://github.com/knickish/heffalump
:windows95: Windows 95
https://github.com/meyskens/mastodon-for-workgroups
@ichigo_chocolat 七上八下睡眠法
@everythingturnsnull 看來只能忍痛賣個低價了
关于微博上那条小红书算法工程师访谈的,看到有人提到这个上瘾机制(一开始赢,然后打压,再然后创作型用户会试图迎合算法)类似电子赌博机培养赌瘾。有点想到之前上Surveillance and Social Control课上谈赌博的near-miss概念(Natasha Schüll的Addiction by Design,中译本《运气的诱饵》),把用户钩住的是“差一点点我就赢了”的遗憾:在需要摇出三个花的老虎机上,显示两个花和零个花在结果上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什么也没赢到,但用户心理落差区别是巨大的。这种“再努力一下就可以”的幻觉override了用户果断转身离开及时止损的理性计算。或许让创作型用户“上瘾”的不止是提供了“被关注”这个target,还有“almost能玩转算法”这个process(我估摸小红书的“打压”力度是选择在一个非常精巧的平衡状态)。
另一方面,正如Natasha Schüll在Addiction by Design中观察到老虎机上的赌棍们并不总是追求“赢”、甚至有时候并不想赢(“赢”反而打乱了他们“继续玩下去”的flow),我觉得“上瘾”小红书的人恐怕也不全是为追求关注和流量来满足自恋。以“想成为网红”来概括所有人就跟同人女搞耽美都是因为三次元有缺失的论断一样可笑。
以及,就像赌博成瘾永远不是赌场(包括赌博机设计者)和赌徒两者之间的问题,小红书的所谓成功也不可能是小红书平台(乃至大平台体系)和用户两者之间的问题。强调“成瘾设计”把责任归给了邪恶的平台(可能还有逐利的资本家),强调“隔绝网络的能力”、“(宁静)强大的灵魂”之类把责任归给了不够聪明的个体,强调“时代的焦虑”把责任推给了抽象的时代(实际上是一种免责),然后我们失去了追问“已经很聪明的人们试图在这个(虽然很糟糕的)地方得到什么他们在别处无法得到的东西”的机会——审视更大的社会环境出了什么具体问题的机会。
- Pronouns
- She / Her / Hers
- Blog (zh)
- https://asaba.sakuragawa.moe